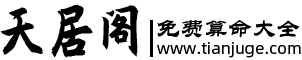每个名字都有特殊的含义、名字在偏僻农村环境就是个代号而已
时间: 2017-10-19 22:35 来源:
名字,顾名思义,就是一个人或物的名称,是特定时空下一个人或物区别另一个人或物的名号而已。放大一个空间,就不一样了,一个极普通的名字,在一个不大的城市里居然有1300余人。名字凸显的是特定的时空,特定圈子里的名号。在中国一般都有两个名字,出生时的乳名或叫小名,还有一个是处世立业的官名。
我的记忆里,乡下起名字就像构成乡村的元素一样,充满乡村野味。叫什么的都有,李粪棒、张狗胞、马粪蛋、猪毬子,驴鞭子、狗蛋子、恶霸女子、黑蛋女子等等,要么是以甲干地支命名,马甲申、李庚午、王丙辰等等,弥漫着乡下的生活气息和甲干地子的轮回。后来知道启丑名字,是为了以丑驱邪,为孩子健康成长。说来也是,那时农村医疗条件差,孩子成活率低,孩子生下来,弱不禁风,都说村子死娃娃沟里鬼叫唤,对于那个环境下的父母来说,取一个驱除疾病的丑名字是最贴心的安慰。
名字本就是代号而已,村子上有怪怪的名号,有个叫赖蛤蟆的人,一叫就是一辈子,去世时才知道他姓陈。有个叫“但是”的老汉,我们一直以为他姓旦名是,谁也没叫过他的真名,直道去世了,讣告上才知正名字。原来是解放后他是贫农代表,让讲话,他学着干部的口气,讲了十几个“但是”,句句不离“但是”二字,也不知道说了个啥,群众自发把他称呼“但是”。
名字在偏僻农村环境就是个代号而已。蒋经国在赣南当专员时,听到一个土财主娶了20多个老婆,苏联学归,血气方刚的蒋经国直奔土财主家,欲杀一儆百,推行新风俗。不料土财主把这些取名字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·····二十几个老婆叫来,有提犁头的、有拿铁锄的,个个粗壮耐劳,没有窈窕淑女。待他问名原因,原来都是他迎娶的都是能劳动的寡妇,长工身份时,这些人对农活不安心,财主就以娶妻为名义变为家室,为共同搞好这个家庭农牧大企业的一种方式。为了好派活分工,原来的名字不叫了,简化为甲乙丙丁的称谓。蒋经国听了就气消了,劝解让妇女改嫁就是。山大沟深的地方,也是一种生存生产方式,这些女人的名字在那个环境下已经不重要。
我家族名字,上辈就不说,我辈的小名就不好听,十多个弟兄全部以“毛”字命名,大毛、二毛、三毛、岁毛、毛能、毛熊、毛旦、毛娃等,给女子起的名字也随便,下房里女子,上房女子,后院里女子。大女子、二女子、三女子称呼即可。都说爷爷是个城里读过书的秀才,为何一个名字都不会起,等我上了小学高年级,认得墙上的分粮公布或者选民登记,父辈的忠字头后面依次是全、智、慧、奎、贤,都是富涵文化的字,三个姑姑也是绣字开头,依次是梅、荷、莲,对号才知道这些土哇哇小名后面其实有个富涵深意的正规名字,农村人叫官名,官名不是为了做官,就是和公共事务打交道的名字,缴税交粮、征兵服役、选民登记等等都得和官方打交道,就得用官名,土哇哇的名字官方也不好记。当然也寄托着父辈对下一代的期望和训导。进入新时代,名字就顺自愿自由,成了小家庭自愿的事,而我父辈们依然定了个平字尾,意味着期望家里清吉平安之意,清、吉、建、新、望,我的名字也就因此成了建平。那时候最怕有人知道父母的名字,尤其直接称呼大人的名字,感觉是最为恶毒的骂人。朱元璋当了皇帝后,有几个一块玩大的少年玩友,感觉想占皇帝的光彩,为表示亲切叫了朱元璋的小名,结果被杀了头。叫名字也是惹祸端的。
名字在小孩子的心中永远是神秘的,记得一个假日的午后,一帮孩子聚在我家院子里玩,他们谈起各自奶奶的名字,一个说奶奶的名字是一种水果,其他孩子就将水果一一列举,苹果、梨子、石榴、桃,当叫到最后的桃时,孩子大声惊呼:“唉,气死人,知道了”。她们竟然哭了起来。又一个的孩子,说他奶奶的名字是一种花,于是一群孩子列举几十种花,都说不是,他提示说,天上下的。大家异口同声:雪花。他也一下子紧张起来,弟兄为此打起架,哭闹成一窝蜂,我好不容易才平息这场孩子的名字风波。
我在初中时,也闹过改名字的风波,那是学了高尔基《海燕》的文章,初步介绍高尔基的名字,阿列克赛·马克西姆维奇·别什可夫。大家感到外国名字的好奇,十多个同学张罗着给自己重起名字,一个姓杜的同学给自己起名:“杜亚斯高尔巴”,一个姓牛的同学给自己取名:“牛英道”,牛在英雄路上奔走。还有一个姓杨的同学改名一个戏剧人物杨延景,我对秦腔戏热爱,崇拜诸葛亮,改名祁亮,还有有个秦腔好者改名刘备,十几个同学都改了名。并且商量同时写在作业本上,开展了一场名字政变,结果被班主任骂得狗血喷头。记得是先从“杜亚斯高尔巴”开始的。老师问:“这班上什么时候进来了外国学生?”紧接着点名,齐茬茬点了改过名的人,让站起来。就从“杜亚斯高尔巴”骂起:“你不得死的跳里,前几天修梯田刚土压死过人,你也想杜亚斯。土把你压死,问你大人咋弄,你大人都不可惜,说:“扔吧”。没出息,起的名字多难听。”然后骂牛英道:“干脆把你就叫牛鞭子多好。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我们改戏剧人物名的,吓得心里打鼓,老师却没有骂:“这是学校不是戏台,点名以为唱戏哩,下来改过来。”就这样改名风波被骂压下去,一一打回了原形。
再一次班上大变名字是初中毕业的时候,那时候位于县城的师范是乡村孩子的清华,不复读是考不上的。而制度又不让复读生考,好在那个时候没有身份证,就给应届的好学生换名字,考上更好,考不上复读再用原名,以逃脱制度设计,而这种更名是班主任和校方保密进行,统考成绩出来前高度保密,防止有人告状,成绩公布定型后,才知道谁对应的谁。就这样一夜之间我班上的十多个好学生,全部由老师秘密命名,结果统考后,只有一个复读上师范,村子里考上了一个师范大学生,有了期望,我们几个就上了高中,就建立了档案,这次校方的秘密命名,就成了同学们永久的名字,档案建立,身份证出现,也没有一个再回到了原名。我在县城高中,老觉得新名字不习惯,刚开始点名还反应不过来,父亲和亲戚进城看我,打问建平时学生都不知道,问了半天直到我下课。父亲对改名很生气,我说明原因,并说了几个改过名的同学,他才明白。说:“也好云彩的云,很好记的。”总体是五个同学改成一个字的:文、理、学、云、英,六个同学改为两个字。
后来改过名的这些同学相继都走向工作岗位,我们还不时和老师坐坐,说起那些秘密的改名。其实都是随机的,想起啥就取啥,看到窗外一片云,就变成我的名。这个名字陪伴我上完中学,读完大学,陪我工作,吃苦和耐劳,陪我发表文章,陪我进步,也陪我忧伤。陪我慢慢长大,有时陪我招风接雨。
写写文字,出本书,主要是给自己心灵的交代,实现耕耘心田之乐。给朋友的签名送阅时,偶尔用了油笔,一文友领导建议注意点文人雅趣,买个签字笔,刻个章子,我就给自己刻一方章子。一则是送书盖章,二则我是个购书匠,到那里去总购买一堆书来,购买时心血来潮,下决心读书,每一回买书回来,我都喜欢在书上写几句话,盖上章子。然后有些就看一些,有些就无时问津。刻了云字章,用了一段时间,觉得少了些什么,一时浮气上升,有种脱离大地之感。细想起来,我把乡土的建平忘却,忘记本根的我就像漂浮的云气,于是又买了块章料,到兰州文庙摊点刻了建平章,两块章子放在一起,相互牵制着,方才心安。乡土的那个建平,才是我立命的根和安稳的魂。。
人类进入网络时代,所有人的名字都上了网络,网络的名字都对应着一个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。我的名字就很有意思,我名字的山泉水有,酒店也有,作家好多个,有人以为一个女作家是我,读了女做家的好多教育学文章,并推在朋友圈,我居然不知道,后来才知弄错了。网络已经把人间的名字的雷同点整合起来。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。那天回家有点饿,突然听到一个母亲声音呼叫我名字吃饭,出来时发现是唤她女孩吃饭,和我一个名字。我已经好久听不到母亲的呼喊名字叫吃饭了,想起了母亲叫我吃饭的声音,那天我思考了半夜。
有时我想,如果地球是个大树,网络上的人就是大树长出的果子,这些独具特色的名字。“习相近,性相远”的果子是互通的,又是隔离的,是无界限的,又是成圈的,是成群的又是分离的,他们时而进入,时而撤出,时而交流,时而沉默,时而喧嚣起来,时而风平浪静。细细思考,喧嚣的往往是那些走出山村后的新名,而那些本真的带乡土的小名却是安静的。那才是让我灵魂安静下来的名字。写些自己灵魂往事,无关乎他人,而那个官名,因为自身的特质及对文字的自幼挚爱,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,与网民的审美、审丑、娱乐、臆想、品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,不小心会变成过眼的浮云,唯恐自己被网络推起轻浮得飘起来。所以在寂静的雨夜,我会把发烧的头淋在雨里,走好长一段的夜路。在醉酒后的早晨,我会反思追忆自己的醉话,体会人心的冷暖,纠正自己的错误。或许烦恼缠心时,回一趟老家,站在父母的坟头,看看自己那个的方位,就会明白名字与我灵魂的关系,与那一片乡土的关系,就会顿悟生命的底线。从热火处退到清凉的地方,就会知道名字背后还有个名声,饱含着做事的法则和处世的良心。就会明白守着方正的官名履职尽忠,握着乡土的乳名悟心做人。
我说过写作是一种病,一种让内心肿胀发痒的难受病,除了显示自己的酸楚和软弱外,不为出名也不为了表现什么。干着,想着,走着,熬着,也就有有篇篇文字出来,明知名字是种累,然而又签上名字,发了出来。
宝宝起名
- 上一篇:姓名与环境和时代的配合应用
- 下一篇:没有了
- ⋅ 每个名字都有特殊的含义、名字在偏僻农村环境就是个代号而已
- ⋅ 同样是王菲的女儿,为何李嫣的能量远超窦靖童?
- ⋅ 姓名与环境和时代的配合应用
- ⋅ 爸妈怎么给宝宝起名才能响亮好听?而这些名字真有才
- ⋅ 这样给宝宝起名,宝妈可真是实力坑娃,你当初怎么给孩子起名的
- ⋅ 王者荣耀算什么,有女孩儿名叫“黄蒲军校”
- ⋅ 起个旺运的微信名字,要注意哪些事项?
- ⋅ 全国重名率最高的100个名字!看你的名字中枪了吗?
- ⋅ 奇门如何起名:论名字的重要性
- ⋅ 人如名片,见名片如见其人!谈一张名片的讲究
- ⋅ 独家解读:为什么俗话说“不怕生错命,就怕起错名”
- ⋅ 没事给自己起个名字,可以锻炼创新性思维
- ⋅ 中国最尴尬的四大姓氏,排第一的你肯定想不到
- ⋅ 很多孩子父母给起名不重视吉凶,就这样被爹妈给坑了
- ⋅ 为什么说扶不起的阿斗,用姓名学看刘禅这个名字怎么样
- ⋅ 宝宝起名参考汉字形体的原始美感、中国汉字博大精深